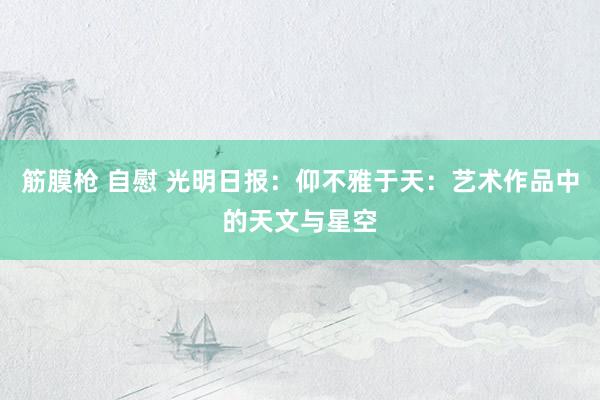

本年2月,寰球领域内出现了包括月掩土星、金星伴月、月掩火星、“七星连珠”等天文景象,激发了多半关注与研究。亘古亘今,东说念主们对天际总抱抓着斥逐的思象与委用,斗转星移,轮回往返,春秋代序,生生握住。古东说念主们“仰不雅于天,俯察于地”,通过对天象的不雅测制定历法、设建都城、建构文雅。辞全国艺术史中,天象是一个迫切的母题,艺术作品中的星空不仅是东说念主类探索外部全国的明证,亦然不雅照内辞全国的记录。

彼特拉克《时间的获胜》(局部)
早期建筑:与天象喜忧关连的艺术
建筑是一种刺眼选址、处所、材质和采光的在地艺术。在中国古代词源学中,“建筑”的“建”字即是从天象不雅测中发展而来的。一年之中,北斗七星辰对什么柄旋转,循序指向十二辰,称为“十二月建”,农历月份即由此而定。在各大文雅的源泉,早期建筑的选址与建造都与天象喜忧关连。
中国的古代建筑大多严格对应天象。早在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化古迹中便有不雅星台和呼应日行规矩的四方祭坛。以瑶山祭坛为例,方形祭坛的四角标的恰恰指向夏至和冬至日的日出与日落标的,从祭坛中心,不错无遮挡地不雅测到无缺的日行轨迹。古代的皇室建筑群对天象与处所的测算与纳降则更为严谨,颐和园中的十七孔桥,每当冬至日前后的傍晚时辰,太阳落于最低点,阳光照耀标的简直与湖面平行,日落余光会循序穿透桥洞,将十七个桥孔的侧壁照耀得通体透亮,伴跟着日落时空气中的尘埃和水汽,酿成“金光穿洞”的冬至奇景。
其他古代文雅的建筑群中,基于对日出和日落的精确不雅测进行相应想象的案例亦有不少。英国南部的斯通亨奇是新石器时期的艺术作品和历史遗迹,建造年代可纪念至公元前3100年驾御。诚然刻下一经倾颓,但在其原始景色,这个巨石阵最外围有一圈壕沟,里面包含了几层齐心圆胪列的石圈,最高的石圈底本由30块立正巨石组成,巨石顶上置有相接的横条石。东说念主们对斯通亨奇的建造样式和用途有多种估量,有天文体家以为斯通亨奇是不雅测天象的实体参照物,最外圈的石阵可平分为8份,八个平分点辩认对应了正南、正北、日夜瓜分点日出、日夜瓜分点日落、夏至最北端月出、夏至最南端月出、冬至最北端月出和冬至最南端月出的标的,内圈的石窍则可用于斟酌日食。
在好意思洲,古玛雅东说念主不仅为后世留住了复杂的翰墨体系,其天文和历法系统也额外练习,这在古玛雅建筑中有直不雅的体现。古玛雅的城市建筑包括宫殿、天文不雅测台、金字塔神庙等。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玛雅遗迹奇琴伊察的中心,有一座玛雅文雅焕发时期的金字塔建筑,即卡斯蒂略金字塔(也称为库库尔坎金字塔)。它是祭祀羽蛇神的神庙,羽蛇神在古玛雅文雅中是太阳的化身。该金字塔底座为正方形,四个坡面上的门道朝向正南、正北、正东和正西四个标的,四面的台阶各有91阶,加上最顶部的一层系数365个台阶,恰恰是哈布历(以365天为周期)中一年的天数。52块有雕镂图案的石板象征着玛雅日期中以52年为周期的轮回。每当春分与秋分日,日出或日落之时,金字塔拐角的轮廓在北面门道上的投影如同蛇身,与门道底部的羽蛇神头像恰恰相接,酿成无缺的蛇形图案,这一切显著都过程了用心的谋略和想象。古玛雅东说念主极为嗜晴天文数据,金字塔的想象处处呼应天文和历法的数字规矩,体现出古玛雅文雅的寰宇不雅念。
说到金字塔,不得不提全国上最著明的金字塔群——位于尼罗河滨的古埃及金字塔。五千多年前,古埃及东说念主的天文和数学一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们很早就字据尼罗河涨落规矩进行星座不雅察。古埃及东说念主将尼罗河视为星河在大地的倒影,并在尼罗河滨建造吉萨金字塔群,呼应星河附近的星座,其中最引东说念主注计算三座金字塔辩认为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孟考拉金字塔。20世纪80年代,有东说念主发现这三座金字塔的相对位置与猎户座的腰带三星(参宿一、参宿二、参宿三)相似,建议了“猎户座关联论”,以为金字塔的选址参考了猎户座的星象位置。21世纪初,东说念主们发现除了排各位置上的呼应以外,这三座金字塔的高度恰恰对应了猎户座腰带三星的亮度,也即是说,最亮的那颗星所对应的金字塔高度最高。
吴梦菲 反差不管石阵、祭坛如故神庙,它们的建造都反馈了东说念主类先民对天体不雅察的高度存眷与精确谋略,这是从基础的活命需要启航的。因为在尚未发明电力的时期,恰是太阳、星空和火带来了光明,使先民们得以“看见”,这也成为东说念主类行动的基础与前提。
纸卷、泥板与石刻:陈腐的星图
在漫长的东说念主类文雅史中,不管东方如故西方,东说念主类对天际的思象与探索从未罢手。从起始的肉眼不雅察到星盘、日晷和浑天仪等不雅测器用的发明和使用,古东说念主为后东说念主留住了多半对于天际的视觉图像和文本记录,星图即是其中之一。它是东说念主类对恒星不雅测的一种形象记录,也被称为“星星的舆图”。它既是东说念主们进行科学探索的历史记录,亦然东说念主们对远方星空的艺术抒发。

伽利略《月球素描》(局部)
全国上已知最陈腐的平面星图是一幅来自敦煌藏经洞的中国纸卷。这卷“敦煌星图”又称为《敦煌星图甲本》,是敦煌经卷的一部分,绘画年代可纪念至唐中宗时期(公元705—710年)。“敦煌星图”客不雅且精确地展示了北天极隔邻的星空,描写出包含1339颗恒星、257个星座的排布,比意大利天文体家伽利略借助天文千里镜完成的星体不雅测早了800多年。
长沙马王堆的三号汉墓中发现了邃密的天文体文章,后被天文史学者称为《天文鼎沸杂占》,该文本图文并举,绘画了包括恒星、彗星等各类星象图约250幅,其中包括31幅彗星图像,是全国上保存最早的对于彗星描画的珍稀史料。也有学者以为早在富商时期,咱们的先人就一经把带着尾巴的彗星用象形翰墨刻在了龟甲上。
19世纪末,在尼尼微(亚述都城之一,位至今伊拉克境内)亚述巴尼拔国王的地下藏书楼,东说念主们发现了一块盘形黏土泥板,泥板名义有极大损毁,据分析,现有的刻纹绘画的是公元前3300年好意思索不达米亚上空的星象,体现了古苏好意思尔东说念主对星象的不雅察和联结。代表星空的泥板圆面被均等地划为8等份,其上猎户座和“V”字形的金牛座图案明晰可见,驾御的楔形翰墨则纪录了相应的星座信息。这是两河流域文雅对星图的较早描绘。
在古埃及文雅留住的对于天际的视觉艺术中,位于丹德拉哈索尔神庙顶部的黄说念十二宫雕镂作品是较为独特的作品。这是已知最早的黄说念十二宫图像。黄说念是指地球上的东说念主不雅察太阳一年内在恒星间所走的视旅途,黄说念两侧的区域即是黄说念带。黄说念十二宫是沿黄说念带分散的十二个星座区域,发祥于古巴比伦东说念主对天际中星座的长期不雅测和占星术应用,他们将黄说念分红各30度天区的12等份,称为十二宫。哈索尔神庙的这块黄说念十二宫浮雕出现于古埃及的托勒密时期,有学者料定浮雕的年代为公元前52年。在浮雕中央圆盘中,中枢位置画有朔方星座,四周围绕着黄说念十二宫的对应标记,符番外围附近手抓物件的微型东说念主像代表着行星,圆盘最外围有序胪列的是拟东说念主化的36个黄说念带分区。由此可见,彼时的古埃及天文体早已趋于圭臬化与精细化。
诚然星图的出现最早发祥于各个陈腐文雅的天象不雅测,谋略标准和绘画标准各有不同,但在并吞派星空下,它是东说念主类灵敏的共同见证,亦然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详细视觉艺术。
绘画:科学带来的花样
伴跟着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天文体转变、帆海大发现和东说念主文精神的醒悟,东说念主类自身的主体性力量被强调,看似鸡犬相闻的天际迟缓褪去了神性的光环和玄秘的象征,拔帜树帜的是去高明化的客不雅记录与目田的艺术创作。因此,在中叶纪、文艺回答和发蒙通顺时期的艺术中,星空呈现出不同的视觉神态。
第一次对彗星进行赤诚描写的作品来自意大利画家乔托。据载,乔托在1301年见到了哈雷彗星,并于1305—1306年为斯克罗威尼礼拜堂南墙绘画湿壁画《东方三博士来朝》时,对其进行了精确描写。这颗庞杂的彗星出刻下画作上方的蓝色天际中,被乔托描画为伯利恒之星。和日食月食一样,彗星的出刻下通盘这个词中叶纪都被东说念主们以为是不详之兆,络续与干戈、夭厉和弃世关连联。虽生于中叶纪晚期,但鉴于乔托对当然的精确发扬,艺术史家也将其视为意大利文艺回答的第一位画家。
手手本是中叶纪时期迫切的视觉艺术载体。在多半手手本案例中,来自林堡昆仲的《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它是国外哥特式泥金掩盖手手本,大略完成于1412—1416年间,书中包含66幅大型致密画及65幅微型致密画,其中最引东说念主关注的是12幅月令图,画作描写了从一月到十二月东说念主们的干事场景。月令图的上半部分是半圆形的天穹,对应当月的星座与古罗马传说中的天使。以《十月》的上空为例,驾着马车的太阳神阿波罗正将太阳托举至天际,外圈的星空图像中是天秤座和巨蟹座的星座标记,每个星座对应天际圆周的30度角,最外环的数字代表了刻度。作家另外绘画了一幅黄说念十二宫星座与东说念主体部位的对应图,从位于头部的白羊座到位于脚部的双鱼座,星象与东说念主体互相呼应。在其时,东说念主们以为黄说念星座诓骗着体魄各个部分的健康,这幅插图也成为中叶纪医学占星学的迫切图像文本。

利弗·弗斯舒尔作品《鹿特丹上空的1680大彗星》
到了文艺回答时期,对天际的描写和对星座的沉沦在艺术家群体中更为盛行。被称为“东说念主文概念之父”的彼特拉克是意大利诗东说念主和东说念主文概念学者,很少有东说念主关注的是,他同期如故一位技法杰出的画家,在寓意体长诗《获胜》中他就加入了我方的画作。在一幅名为《时间的获胜》的插图中,太阳在满天繁星中开动,横跨天际的黄说念带上绘画着十二星座的对应图符,这是一个并不合适内容情况的思象性描写,抒发了东说念主类的光泽与天际中众星的狂欢。
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文艺回答时期与达·芬奇皆名的科学家与艺术家,亦然第一位绘画古典星图的画家。1515年,他在数学家约翰内斯·斯塔比乌斯和天文体家康拉德·海福格尔的匡助下,完成了欧洲第一部印刷星图的绘画,在其中两幅木刻版画中,他全面展示了黄说念带以北及以南天球上的通盘已知星座。诚然这两幅星图依然基于托勒密辑录的星座体系,但海福格尔更新了这些星体在1500年出现的位置,丢勒字据坐标系统作了准确制图。这两幅天体图是在欧洲公布的最陈腐的版画星图,它们并非出于地球上的不雅测视角,而是基于天球外部的俯视视角完成,因此在北天体图中出现的星座形象都呈现为东说念主体背部,南天体图则出现较多的空缺区域,标明其时东说念主们对南天星空常识的相对匮乏。
到了发蒙通顺时期,珍视理性与科学的风潮涌动,视觉图像中的星空呈现出十足不同的神态,东说念主们对星空的描写趋于圭臬化和科学化。当作天文制图的岑岭期,17世纪出现了《寰宇范例》《赫维留星图》等邃密的星图集与天文文章。这一切都与天文不雅测器用的发明有着告成谈论。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第一台天文千里镜,将东说念主类眼力领域延展至云霄以外,使也曾鸡犬相闻的星空变得确切而具体。以前年末,伽利略字据不雅察所得完成了一幅《月球素描》,以邃密的笔触呈现了月球名义多样险阻结构及明暗对比下的盈亏景色,第一次让东说念主类看清了月球果长远神态,这亦然艺术史中的第一幅天体素描写生。次年,伽利略出书了《星空使臣》一书,书中收录了他不雅测到的月球图像。

文泽尔·哈布立克作品《星空:尝试》
到了17世纪中叶,天文体家乔瓦尼·多梅尼科·卡西尼在长期不雅察后发现木星上的风暴时,也相似采用以手绘的样式记录了1665年、1672年和1677年通过千里镜看到的征象,其后有学者以为这些绘画记录的恰是东说念主们熟知的木星大红斑,但此不雅点仍具争议。1666年,卡西尼被路易十四任命为新法国皇家科学院成员,次年担任新诱惑的巴黎天文台台长。其时的巴黎舆图销售商之子尼古拉斯·德·费尔刻制了一组巴黎天文台的版画。咱们在其中一张画作中看到其时天文体家们的不雅测征象,大型天文千里镜架在天文台外的深渊上,天文体家们正在不雅测月食的发生。
彼时的艺术家们对天体包括对地球自己都充满了极大的研究兴趣兴趣。以“荷兰小画派”的代表画家维米尔为例,他在光学、制图学、音乐、地舆学和天文体等规模都有膏腴的常识鸠集。绘画于1668年的油画作品《天文体家》,从定名上就体现了他对其时先进科学工夫的关注。亦然在发蒙通顺时期,绘画作品中出现彗星的场景不再伴跟着东说念主类的惊险、疾病与弃世。相较于托勒密时期所以为的不详预兆,彗星在1705年赢得了天文体上的正名,哈雷发表《天文体对彗星的简介》,将其讲解注解为一颗具有周期总结特质的天体。是以在另一位荷兰画家利弗·弗斯舒尔绘画的油画《鹿特丹上空的1680大彗星》中,一颗从天而下的彗星出现于鹿特丹上空,城市中的东说念主们并未蹙悚失措,而是绘身绘色地藏身不雅望,甚而提起了手中的千里镜不雅察。
如若说发蒙通顺时期是星空图像的理性化与科学化时期,那么艺术创作参预当代全国后,则呈现出纷纷密样的视觉方法,天际好意思术、星空艺术、寰宇电影等日出不穷。脱离于理性的圭臬和规制,艺术中的星空重新成为艺术家笔下带有斥逐颜色和主不雅意趣的图像主题。
艺术史上最著明的星空当属梵高的《星月夜》。比梵高小10岁的蒙克,相似曾生活于巴黎并深受印象派影响。他的油画作品《星空》是对梵高《罗纳河上的星夜》的致意,仅仅蒙克笔下的星空暴露着如同极光般的大面块绿色,举座呈静谧与深千里的基调。与蒙克同为发扬概念画派的文泽尔·哈布立克也绘画了星空主题作品,他的《星空:尝试》使东说念主仿佛踏进星群,广大星辰与天体在星河中的旋转律动体现出一种高明的范例感。

卡斯蒂略金字塔在独特光照时刻酿成羽蛇神的“光影蛇形”
跟着东说念主类第一次登月的到手,天上的星星成为不错抵达的此岸,艺术家们不再甘于像伽利略或卡西尼那样,仅仅将星体视为被不雅看的客体或他者,而是将东说念主的形象安置到星体之上,强调东说念主类自身的“在场”。举例,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月球行走》定格了阿姆斯特朗登月的经典历史须臾,以波普艺术的格调化科罚,强调东说念主类与星体的共在。某种风趣风趣上说,“登月”是一个东说念主的小小一步,却是东说念主类的一个庞杂飞跃,“登月图像”亦然漫长的全国艺术史上,东说念主类星际巡游和天际思象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从建筑艺术对天象的呼应,到视觉艺术对星空或理性、或理性的描写,天文体与艺术酿成了如同双子星般的共生关系,咱们头上的这片星空迟缓褪去未知的面纱,图像中的星空也不再仅仅一个被眺望的对象,而是成了可知、可探、可及的寰宇。
(本文图片均为而已图片)
作家:陆颖 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汲引
开端:《光明日报》(2025-03-27 13版:国外教科文周刊·国外文化)
剪辑:蒋红跃
